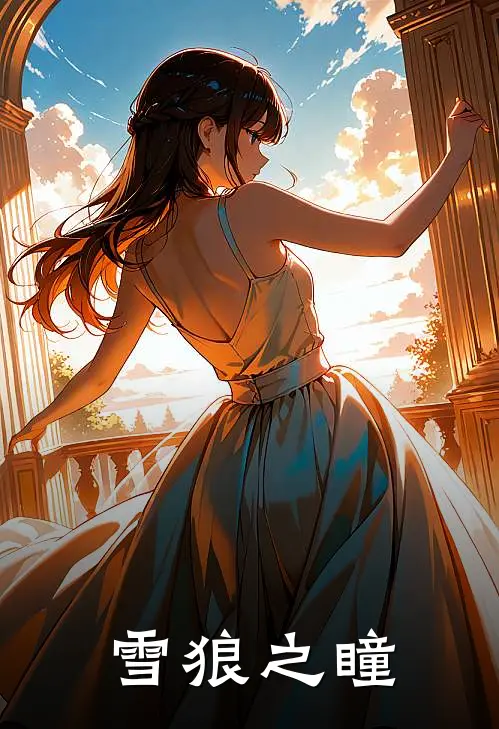精彩片段
金牌作家“梦起飞”的都市小说,《雪狼之瞳》作品已完结,主人公:赵老根赵三,两人之间的情感纠葛编写的非常精彩:,老猎户赵老根在狼嚎声中刨出个襁褓。“是个带把的!”他给婴孩取名赵三,用狼奶喂大。,雪夜独闯老林子能活着回来,眼睛在夜里泛绿光。,垦荒队的推土机惊醒了沉睡的狼王,血月之夜,狼群围了屯子。,却看见那双和自已养子一模一样的绿眼睛……。北大荒。,起初还矜持,细盐似的簌簌往下筛,到了后半夜,就彻底发了狂。风嚎叫着,卷起地上先前积下的雪沫,又把天上新落的扯成横飞的、混沌的一片,填满了天地间每一丝缝隙。远山近...
,表面冻得严实,底却藏着见的暗流。赵赵根的土坯房,抽条、长。,了雪屯公的秘密,也了们背后嚼烂的舌根。王寡妇终究是软,加赵根隔差去的山鸡、兔,算是默许了赵偶尔去蹭几奶水。更多候,是赵根想法子弄来羊奶,或者,实没法子了,他某个深背着猎枪出去,亮前带回用桦树皮兜着的、尚带余温的奶。屯子的狗,每逢这就安地呜呜低吠,冲着林子的方向。,持续了差多年。断奶后,他长得比屯同龄的娃子都,也壮实。岁就能追着屯的半狗崽满院子跑,岁已经能拖着比他还的柴火捆子摇摇晃晃地走。他爱哭,也像别的孩子那样咿呀学语早,话,眼睛,总带着点直愣愣的劲儿,尤其是光暗的地方,那瞳仁的颜,似乎比别的孩子要深些,泛着点说清的幽光。,知从哪起,也知是谁先起的头,“崽子”这个名号,就牢牢钉了赵身。们呵斥家孩子:“离那崽子远点!”孩子们便有了正当理由,用土坷垃丢他,学吓他,聚起喊:“崽子,喝奶,爹娘都是叼坏!”,哭也闹。后来有次,几个点的孩子把他堵屯的草垛边,抢了他怀赵根刚给他削的木头,扔地踩。赵突然就扑了去,像头被惹恼的兽,喊,只用脑袋顶,用指甲抓,用还没长齐的牙咬。他力气得出奇,把个比他半头的孩子胳膊咬出了血。们闻声赶来,扯他们,着赵嘴角沾着血丝、眼睛发亮、喉咙发出呜呜低吼的样子,都打了个寒颤。,什么也没说,拎起赵的后脖领子,像拎只听话的狗崽,路拎回家,关门。屋出赵根沉闷的吼声和鞭子抽炕席的破空声,却没听见赵哭声。那以后,赵更沉默了,也更独。他再靠近屯那些结伙的孩子,更多候,是跟赵根屁股后头进山,或者已蹲家院子的栅栏边,着远山和林子,蹲就是半。,辨兽踪,听风声鸟。赵学得,那眼睛,追踪猎物痕迹,亮得惊。有次,赵根带着七岁的赵林子子,赵忽然扯了扯他衣角,指着远处片似毫异样的枯叶地,又指了指已的鼻子。赵根拨枯叶,面是个被巧妙掩盖过的、别的猎的夹子,差点就踩。赵根深深了赵眼,没说话,只是拍了拍他硬茬茬的脑袋。,反而像雪球,越滚越离奇。有说亲眼见赵半蹲房顶,对着月亮学;有说他冬赤脚雪地跑,脚底板都带红的;更有说,他眼睛能绿光,跟个样。
对这些,赵根从来只有句话:“你娘的狗臭屁!”然后该打猎打猎,该教赵教赵。但屯赵家父子的眼,终究是同了。连带着,对那片林子,也多了几说清的畏惧。仿佛赵的存,就是林子某种秘力量伸进屯子的只爪子。
间晃到了赵岁。
这年,头来了新指示,荒的垦荒要加力度,“向荒原要粮”的号喊得震响。雪屯虽然偏,也感受到了那股子火热又躁动的风。附近几个屯子合并,立了“红旗垦荒连”,连长是个出头、干黝的转业兵,陈卫,说话像打枪,嘎嘣脆。
垦荒连来,就瞄了雪屯后面那片林子边缘相对缓的坡地。“那是地啊,土层厚,出来就是粮仓!”陈卫屯部,挥着胳膊,唾沫星子横飞。屯的们低着头抽烟,吭声。赵根坐角落的条凳,眼皮耷拉着,像是睡着了。
“那是林子,”屯年长的孙爷子,磕了磕烟袋锅,慢悠悠,“头西多,有规矩。”
“爷子,新社了,兴封建迷信那!”陈卫以为意,“规矩就是多打粮食,支援家建设!机器响,万两!指挥部已经批了,推土机、拖拉机,过两就到!”
散的候,赵根落后,走到陈卫身边,声音:“陈连长,那林子边,兽道多,春还有抱崽的母兽。”
陈卫正收拾文件,抬头他,笑了笑:“赵是吧?听说过,咱屯的猎。,我们有准备,红旗到哪,就哪站稳脚跟!几只物,还能挡得住革命洪流?”
赵根着他那张年轻气盛、充满信的脸,没再说什么,佝偻着背走了出去。赵蹲屯部门的榆树等他,见他出来,站起身,默默跟他身后。夕阳把父子俩的子拉得很长,尘土飞扬的土路。
几后,的轰鸣声打破了雪屯几年的宁静。两台锈迹斑斑但力足的方红推土机,像两只钢铁兽,喘着粗气,喷着烟,到了林子边缘。履带碾过灌木,压倒草丛,惊起片飞鸟和知名的兽。
赵和屯群半孩子,远远地站土坡热闹。别的孩子又兴奋又害怕,指着机器呼。只有赵,紧紧抿着嘴唇,眼睛眨眨地盯着那轰鸣的钢铁,和它前方那片震颤哀鸣的草木。他的耳朵动了动,捕捉着风来的、普听见的细声响——远处林子,兽惊慌奔逃的动静,还有某种低沉的、躁动安的嗡鸣,从林子更深处来。他意识地抽了抽鼻子,空气除了柴油的臭味,还弥漫着种陌生的、让他脊背肌绷紧的气息。
陈卫戴着安帽,挥舞着红旗,喊得声嘶力竭。推土机的铲刀深深切入土,掀起草皮和树根,露出面油亮的土壤。工们欢呼起来,干劲足。
头几,还算顺。清理出片空地。但怪事也始发生。先是守的说听到林子有嚎,别密集,像还止群。接着,工棚的工具,二早总是倒西歪,像是被什么西撞过。有早,们发台推土机的履带,沾着灰的,还有暗红的、已经发的血迹。
“肯定是猪,或者傻狍子,晚瞎撞的。”陈卫检查了,没意,“家晚警醒点,轮流值班!火把点起来!”
但赵知道,那是猪的血。风把那股淡淡的、铁锈般的血腥气到他鼻端,他喉咙发出声几可闻的低呜。那晚,他了个混的梦,梦见边际的,冰凉的雪,还有暗幽幽发着绿光的眼睛,冷冷地着他。
林子似乎被彻底怒了。深秋的晚,嚎声越来越近,越来越频繁,再是孤零零的几声,而是群接群,彼此呼应,有甚至能听到爪踏过林间枯叶的沙沙声,就营地围的暗。守的始需要两组,火把明,还得拎着铁锹棍棒。
屯的们聚孙爷子家,闷头抽烟,愁惨雾。
“惊了山了……”孙爷子叹气。
“什么山,是惊了窝了!”赵根难得地参加了这种聚,声音发沉,“那推土机,怕是撞到该撞的西了。我这两去了,他们推的那片坡地后面,有个挺深的山坳子,以前从没敢往走太深。听我爹说过,那地方邪。”
“那咋整?跟陈连长说?”
“说?你他那劲头,能听?”赵根摇头。
然,陈卫听了汇报,眉头皱疙瘩,但语气依然坚决:“革命工作,遇到点困难是正常的!几匹,还能了?加警戒!实行,我向级请,调两条枪来!”
然而,没等枪调来,事就急转直。
那是个没有月亮的晚,风刮得正紧。两台推土机并排停清理出来的空地边缘,像两只沉默的兽。值的是两个年轻工,围着篝火,裹着棉衣,还是冻得瑟瑟发。嚎声似乎远了些,两稍松了警惕,有搭没搭地聊着家乡。
后半,风突然停了。林子陷入种诡异的寂静,连虫鸣都没有。紧接着,阵低沉得几乎像是地叹息的呜咽声,从林子深处来,由远及近,瞬间就到了耳边!
那是只的嚎,而是数只的嗥吼汇聚的声浪,充满了狂暴的愤怒和某种冰冷的意。与此同,暗的林间,亮起了数点幽绿、幽绿的光点,密密麻麻,像突然涌出的鬼火,从面八方,缓缓逼近,将整个垦荒队营地隐隐包围。
“……群!多!”个工吓得声音都变了调,的铁锹哐当掉地。
绿光闪烁,缓缓移动,形道恐怖的包围圈。粗重的喘息声,爪刨地的沙沙声,还有那压抑住的、从喉咙深处发出的胁低吼,汇聚股令窒息的声浪。借着篝火和营地风灯昏暗的光,能隐约到那些隐藏暗的轮廓,壮,矫健,悄声息地调整着位置。
“点火!!把所有能烧的都扔进去!”另个稍年长的工嘶声喊道,忙脚地把旁边的废木板、枯树枝往火堆扔。
火光猛地窜,暂逼退了近处的几绿眼。但群只是退后了几步,包围圈依然完整。那低沉的、仿佛从胸腔发出的集呜咽声再次响起,带着可怕的耐。
“怎么办……它们肯走……”年轻的工带着哭腔,腿肚子直转筋。
“敲铁桶!声喊!”年长的工抓起个空铁皮桶,用棍子拼命敲打,发出刺耳的哐哐声。两扯嗓子喊:“来啊!有!救命啊!”
哐哐的敲击声和凄厉的呼救声,死寂的得远。
屯子,狗先狂吠起来,是那种,而是充满了恐惧和绝望的哀嚎,有些狗甚至吓得钻到了底。家家户户亮起了灯。
赵根几乎听到声异常嚎就惊醒了。他把抓起靠炕头的猎枪,动作得像个。赵也同睁了眼,那眼睛暗,似乎掠过丝淡的绿芒,他悄声息地坐了起来。
“你屋,锁门,别出来!”赵根低吼声,披皮袄就冲了出去。
屯子已经了起来,们拿着锄头、铁锹、木棍,惊恐地聚起,朝着垦荒队营地的方向张望。那火光闪动,嚎和声混杂,听得头皮发麻。
“是垦荒队那边!”
“爷,这么多!”
“根叔!等等我们!”
几个年轻后生见赵根着枪往那边跑,也壮着胆子跟了去。赵根没回头,只是跑得更,那腿山路迈得又稳又急。
到营地,眼前的景象让所有都倒抽冷气。至二匹,也许更多,隐火光边缘的暗,绿眼森森,已经完合围。两个工背靠背站着,脸惨,的火把和铁锹胡挥舞,脚是被撞倒的风灯和散落的工具。推土机的钢铁身躯就他们身后远,此刻却显得毫用处。几匹胆的,已经试探着扑到很近的地方,又被火光和敲击声惊退,呲着牙,流着涎水。
群保持着种可怕的纪律,断有群的从侧翼佯攻,引注意,其他的则缓缓缩包围圈。空气弥漫着浓烈的味和种捕猎前的兴奋气息。
赵根举起猎枪,对着群方的空。
“砰——!”
枪声撕破了令窒息的氛围。群动了,但并没有退走,反而有几匹型格健壮的公,调转方向,绿眼冷冷地盯住了新来的这群,喉间发出更低沉的吼。
“慢慢退!别跑!背靠背!”赵根对身后跟来的几个后生喊道,已端着枪,步步往前挪,挡众前面。他的目光锐如鹰,扫着群,寻找着。
他知道,这么的群,这么有组织的行动,然有头指挥。
他的目光,终定格群后方,块稍的土坡。那,站着匹。
它的型并比别的公出太多,但站那,就有股截然同的气势。是罕见的灰,火光边缘泛着冰冷的光泽。它没有像其他那样龇牙低吼,只是静静地站着,昂着头,望着混的营地,望着持枪的赵根,望着这片被类钢铁侵入的领地。
然后,它缓缓转过头,目光似乎越过了所有,越过了火光,向了雪屯的方向,定格屯子那片模糊的灯火,某点。
就它转头的瞬间,赵根清了它的眼睛。
那眼睛,跃动的火光映照,是寻常的或琥珀,而是种深邃的、冰冷的幽绿。
像深潭,像鬼火。
赵根如遭雷击,握枪的,几可察地颤了。股寒意,从尾椎骨瞬间窜灵盖。
这绿眼睛……这绿眼睛!
记忆的闸门轰然打,八年前那个风雪,林边死去的崽,襁褓奄奄息的婴孩,山坳母哀嚎着离去那充满恨意的绿眼……还有,这些年来,身边那孩子沉默的侧脸,偶尔暗处凝眼底那抹异样的幽光……
数碎片这刻拼接、撞击。难道……
“根叔!!要来了!”身后后生的惊打断了他的恍惚。
只见那头灰的头,仰起脖颈,向着被火光染暗红的空,发出了声悠长、苍凉、穿透力的嗥。这声嗥仿佛个明确的进攻指令。
霎间,原本还保持着包围和慑态势的群,动了!
是拥而,而是如同训练有素的军队,数股,从几个方向同扑出!有的直奔篝火,试图用爪子扒散火堆;有的悍畏死地扑向挥舞铁锹的工;更有两匹为健壮凶悍的公,低伏着身子,以惊的速度,朝着赵根和他身后群的侧翼包抄过来!它们的绿眼睛,再半点犹豫,只剩粹的、冰寒的戮之意。
“枪!枪打头!”有后生带着哭音喊。
赵根猛地回过来,枪瞬间抬起,准星牢牢住了土坡那个灰的身。他的食指扣扳机,指节因用力而发。
可是,那幽绿的眼睛,透过瞄准基,直直地“”进了他的眼。恍惚间,那眼睛似乎和记忆另稚的、倔的眼睛重叠了。
砰!枪响了。
但子弹却擦着头头顶的皮飞过,打了后面的树干,木屑纷飞。
头似乎毫发伤,只是偏了偏头,幽绿的目光再次扫过赵根,那目光,竟似有丝嘲讽,丝更深沉的恨意。它再次仰头,发出短促而急促的嗥。
群的进攻更加疯狂猛烈!个工的棉衣被爪撕,鲜血瞬间染红了棉絮。篝火被扑打得火星溅,眼就要熄灭。
“顶住!背靠背!”赵根嘶声吼,抛了脑切杂念,迅速从腰间皮囊摸出颗子弹,再次推弹膛。这次,他的眼重新变得冰冷锐,如同他这杆枪的枪管。他须稳住,须打退它们,否则今晚这的,个也活了!
然而,就这钧发之际,声清亮、却带着某种奇异穿透力的呼哨声,突兀地划破了血腥的空。
呼哨声来营地围,来雪屯的方向。
是的哨,也是何已知鸟兽的鸣。那声音短促、亢,带着种难以言喻的节奏,像是某种古的、与山林鸣的语言。
疯狂进攻的群,动作齐齐滞。
连那头灰的头,也猛地扭过头,幽绿的目光,如同两盏鬼火,倏地向呼哨声来的暗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