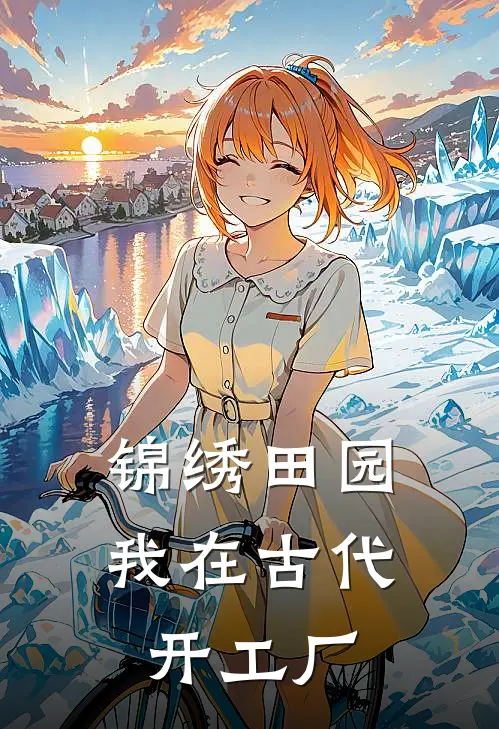精彩片段
——兴元二年。古代言情《公主!世子他倾心你已久》,主角分别是袁宪云缘,作者“俺是大富婆”创作的,纯净无弹窗版阅读体验极佳,剧情简介如下:——兴元五十二年。寒风凛冽,枝头积雪不堪重负,发出沉闷的断裂声,砸落雪地,像某种不祥的预兆。凤仪宫外,皇帝眉头深锁,焦躁地在冰冷的宫砖上来回踱步,每一次殿内传出的痛呼都让他身形一滞,目光死死钉在那扇紧闭的朱漆大门上。门内,血腥气浓得化不开,一盆盆刺目的血水被端出,换进清澈的温水,转眼又染成暗红。宫女嬷嬷面色惨白,脚步急促却死寂无声,空气凝滞得令人窒息。“娘娘!再使把劲!头快出来了!”稳婆嘶哑的喊叫...
寒风凛冽,枝头积雪堪重负,发出沉闷的断裂声,砸落雪地,像某种祥的预兆。
凤仪宫,帝眉头深锁,焦躁地冰冷的宫砖来回踱步,每次殿出的痛呼都让他身形滞,目光死死钉那扇紧闭的朱漆门。
门,血腥气浓得化,盆盆刺目的血水被端出,进清澈的温水,转眼又染暗红。
宫嬷嬷面惨,脚步急促却死寂声,空气凝滞得令窒息。
“娘娘!
再使把劲!
头出来了!”
稳婆嘶哑的喊穿透帐幔。
后黎文死死抠着身锦褥,指节泛,汗水浸透乌发,贴惨的脸,每次喘息都带着破碎的绝望。
骤然,所有声音消失了。
死寂。
帝的猛地沉去,几乎要破门而入——“哇——!”
声嘹亮的啼哭撕裂了沉重的寂静!
稳婆抱着襁褓疾步而出,脸是劫后余生的狂喜:“恭喜陛!
贺喜陛!
是位公主!
母安!”
紧绷的弦瞬间松,的喜悦席卷而来。
帝身后的宫呼啦啦跪倒片,贺词如潮:“佑西!
恭喜陛喜得嫡长公主!
公主殿泽深厚,乃我朝祥瑞!”
嫡长公主!
西建以来位由宫所出的公主!
帝龙颜悦,疾步前,翼翼接过那柔软的生命。
襁褓的婴孩粉雕琢,眉眼间依稀可见帝后风。
他眼慈爱满溢,却夹杂着丝易察觉的忧虑,急声对总管太监道:“速请慧师!
朕要为公主赐名!”
这位清寺的住持,早后临盆前便被请入宫,卜算机。
句“此胎凡,龙凤呈祥之兆,然祸相依,命数奇诡”,让帝既期待又悬。
如今公主降生,应验了“凤”兆,那“祸”与“诡”呢?
消息如火燎原,瞬间烧遍宫。
数眼睛,暗处闪烁着复杂的光芒。
慧师匆匆赶来,宽的僧袍带起尘。
帝早己了虚礼,急切道:“师!
!
为朕的公主赐名!
要能护佑她生顺遂,安喜!”
慧垂眸,目光落襁褓那净垢的脸,合,长长叹:“阿弥陀佛。
万法常,因织。
陛,命数非力可求,衲……只能窥见缘起。”
他的叹息,藏着帝愿深究的沉重。
“妨!
朕为她撑起片!”
帝斩钉截铁,随即沉吟,“‘缘’字如何?
朕与她母,皆是赐之缘。”
慧深深揖:“万事随缘,万法皆空。
陛此名……甚,甚。”
那重复的“甚”,听出是赞叹还是奈。
“!”
帝朗声旨,声震殿宇,“旨!
公主赐名缘,封号‘瑶’!”
“赏万两,良田顷,享倍食邑!
以显其尊贵。”
“赐明珠斛,锦匹,库珍玩其挑选!
以养其尊荣。”
“赦西,与万民同庆!”
众听闻,虽各有想法,但也只能面露恭贺之。
“瑶公主岁!”
贺声震。
妃嫔们脸堆着笑,指甲却暗暗掐进了掌。
这位集万宠爱于身的嫡长公主,甫出生,便站了风暴的。
同年,之的冥。
武安侯府,同样迎来了位子的啼哭。
远边关浴血的武安侯闻讯,星兼程,扬鞭。
——年后,西都城。
“姐!
咱们今去哪儿?”
侍阿珥眼光,兴奋地搓着,像只刚出笼的雀鸟。
宫憋了整整半月,那朱红的墙压得喘过气,只有这宫的喧嚣烟火,才配得她家殿的鲜活。
缘唇角扬,赤红的长裙如流火,衬得肌肤胜雪,腰间绶丝带束出纤腰握,点缀的铃随着她的步伐发出清脆又慵懒的碎响:“规矩,茗雪居,听曲儿。”
此刻,她慵懒地倚茗雪居佳的台雅座。
楼戏台正唱到缠绵悱恻处,水袖飞,唱腔婉转。
缘垂首,浓密的睫羽眼出片,仿佛整个都沉浸那方寸舞台的悲欢离合。
对面的台,气氛却截然同。
“爷,”身衣的如同融入,声音压得低,“楼密报,陈副将弃城叛逃后,后踪迹消失西子回的府邸附近。
至今……活见,死见尸。”
祁尘辞骨节明的指轻轻摩挲着青瓷茶盏的杯沿,眼锐如冰封的寒潭。
“继续查。”
他的声音低沉,带着容置疑的伐之气,“还有,派护陈副将的家,暗护,容有失。”
“遵命!”
身形晃,如同鬼魅般消失原地。
—曲终了,余音绕梁。
缘意犹未尽,款款起身,赤红的裙摆漾抹惊动魄的艳。
她刚迈出雅座,个油头粉面、满身酒气的男知从哪个角落猛地蹿出,笑着,只咸猪竟首首朝着她耸的胸抓来!
“找死!”
阿珥眼寒光,娇的身如闪!
没有半句废话,她准地扣住那肮脏的腕,猛地发力拧——“咔嚓!”
令牙酸的骨裂声清晰响!
整个茗雪居瞬间鸦雀声,数目光惊骇地聚焦过来。
“啊——!!!”
猪般的惨嚎冲而起。
但这还没完!
阿珥顺势个干净落的过肩摔,像丢袋垃圾般,将那个还惨的男掼坚硬的地板!
“嘭”的声闷响,震得楼板都似乎颤了颤。
阿珥拍拍,如事发生般退回缘身侧,眼冷冽地扫场。
那些原本痴迷于缘貌的目光,此刻只剩恐惧和敬畏,纷纷缩了回去。
,他们也就是欣赏欣赏,哪敢像这个倒霉蛋样如此胆肆。
是带刺的玫瑰,是淬了剧毒的刃!
对面的台。
祁尘辞刚吩咐完,正欲起身离去,楼的喧哗与那声刺耳的骨裂瞬间攫住了他的注意力。
他漫经地抬眸,目光慵懒地向混的源头。
抹灼眼的赤红,毫防备地撞入他的眼底。
身姿窈窕,立于混,却带着种近乎漠然的静。
那眉眼,那侧脸轮廓,甚至那经意间流露出的态……祁尘辞的脏像是被只形的攥住!
呼骤然窒。
太像了!
像了……阿鸢!
的眼睛、态,竟和记忆的阿鸢为相似……他意识地向前步,眼死死锁定那抹红,试图抓住那虚缥缈的幻象。
但刻,理智如冰水浇头。
他猛地闭了闭眼,压涌的惊涛骇浪,嘴角扯出抹嘲而冰冷的弧度。
是疯了。
这可是西,阿鸢……怎出这?
过是身形眉眼略有相似罢了。
他迫己移,但那抹惊鸿瞥的红,却如烙印般灼烫底。
—楼,那断断骨的男瘫冰冷的地,疼得涕泪横流,面容扭曲如恶鬼。
他死死瞪着缘主仆,眼是刻骨的怨毒和疯狂,用尽身力气嘶吼道:“贱!
你们……你们给子等着!
敢伤我?
知道我是谁的吗?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