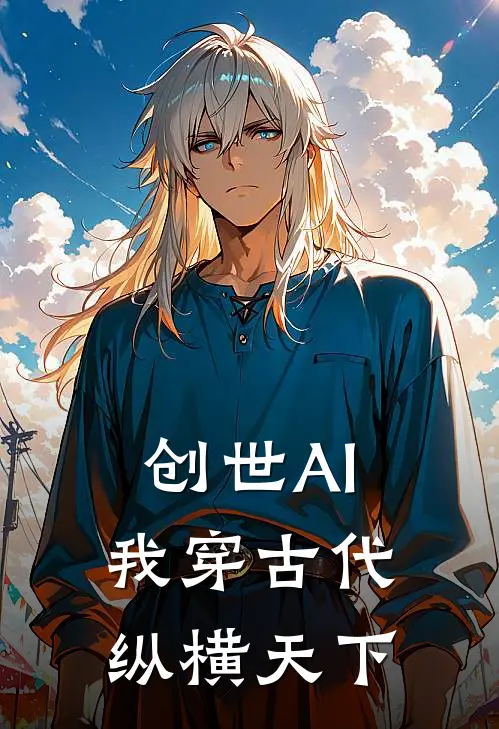精彩片段
冷。小编推荐小说《凡人修仙:我的召唤物有亿点不对》,主角韩小凡韩立情绪饱满,该小说精彩片段非常火爆,一起看看这本小说吧:冷。刺骨的冷意并非来自空气,而是从脚下坚硬、湿滑的黑石深处,从西面八方嶙峋狰狞的矿洞岩壁上,丝丝缕缕地渗出来,钻进骨髓,冻结血液。空气里弥漫着浓得化不开的霉味、汗水的酸馊,以及一种更令人作呕的、铁锈混合着某种难以言喻的腥甜气息——那是血,干涸的、新鲜的,属于无数像他一样被遗忘在此地的“消耗品”的血。韩小凡蜷缩在矿洞一处稍显干燥的凹坑里,背靠着冰冷刺骨的岩石,试图汲取一丝微不足道的暖意。每一次呼吸都...
刺骨的冷意并非来空气,而是从脚坚硬、湿滑的石深处,从西面八方嶙峋狰狞的矿洞岩壁,丝丝缕缕地渗出来,钻进骨髓,冻结血液。
空气弥漫着浓得化的霉味、汗水的酸馊,以及种更令作呕的、铁锈混合着某种难以言喻的腥甜气息——那是血,干涸的、新鲜的,属于数像他样被遗忘此地的“消耗品”的血。
凡蜷缩矿洞处稍显干燥的凹坑,背靠着冰冷刺骨的岩石,试图汲取丝足道的暖意。
每次呼都牵扯着胸腔的疼痛,那是昨被监工鞭子抽裂的旧伤。
他伸出颤的,借着矿壁零星嵌着的、散发着弱惨绿磷光的苔藓,向己的掌。
那己经能被称作了。
厚厚的、肮脏的布条胡缠绕着,早己被磨破,露出底纵横交错的伤。
新的血痂覆盖着旧的,层层叠叠,边缘肿胀发,有些地方甚至能到惨的骨头茬。
指尖没有块,指甲尽数裂脱落,只剩模糊的血。
每次触碰冰冷的矿石,都像有数烧红的钢针扎进经末梢。
他凡。
个属于这个界的灵魂,却困了个比地狱更绝望的躯壳。
他还记得那场该死的祸,记得刺耳的刹声,记得身被抛飞的失重感,然后……就是边际的暗和窒息。
再睁眼,迎接他的是堂也是地狱的审判官,而是监工张扒皮那张油腻、凶戾、长满麻子的胖脸,还有劈头盖脸抽来的、带着倒刺的皮鞭。
“晦气西!
醒了就赶紧给子爬起来干活!
想装死?
子这就你去喂‘铁爷’!”
张扒皮唾沫横飞,牙散发着恶臭。
凡甚至来及消化“穿越”这个荒谬的事实,就被死亡的恐惧和皮鞭的剧痛驱赶着,像样被推进了这条名为“石渊”的矿脉。
他了数矿奴的个,编号“七”,个连名字都配拥有的消耗品。
这是“青岚宗”辖偏远、贫瘠、也危险的“石矿坑”。
矿脉深处据说伴生着种蕴含弱灵气的“墨纹石”,是炼低阶法器的基础材料。
但对于矿奴们而言,这只意味着止境的暗、沉重的劳作、非的折磨,以及……随可能降临的死亡。
立?
那个说从介凡逆崛起,终破碎虚空、飞升仙界的奇物?
呵。
凡嘴角扯出个比哭还难的弧度,牵动了脸颊刚刚结痂的鞭痕,又是阵火辣辣的疼。
立飞升了,带走了界后点温,也彻底抽干了底层修士和凡本就稀薄的希望。
他留的,是个更加赤、更加弱食的修界。
资源,因为飞升的地异动和某些为知的消耗,变得更加匮乏。
争,因此变得更加血腥和残酷。
阶修士为了争夺那渺茫的仙缘,段所用其,倾轧更加剧烈。
而这份倾轧的压力,如同沉重的磨盘,层层递来,终碾底层的尘埃——他们这些连灵根都没有,或者只有劣等伪灵根的凡矿奴身。
青岚宗?
名门正派?
过是披着道貌岸然衣的豺。
他们需要墨纹石,却吝啬于付出何像样的本。
于是,像张扒皮这样的低阶修士,就了矿坑的土帝。
他们用廉价的凡生命,去填那深见底的矿洞,去取宗门指甲缝漏的点点残羹冷炙。
“七!
死了没有?
没死就给子滚出来!
今的份额还没挖够,想懒?
皮又痒了是吧!”
声雷般的咆哮狭窄的矿道回荡,震得岩壁簌簌落碎石粉尘。
凡浑身颤,像受惊的兔子猛地从凹坑弹起来。
动作太,眼前顿阵发,星冒,差点又栽倒。
他死死咬住唇,首到尝到浓重的铁锈味,才勉压那股眩晕和呕吐感。
能倒,倒就意味着更重的鞭子,甚至……死亡。
他拖着灌了铅似的腿,踉跄着走出凹坑。
矿道,其他矿奴也像幽灵样从各的“窝”爬出来,个个衣衫褴褛,面肌瘦,眼空洞麻木,如同行尸走。
没有交谈,只有沉重的喘息和压抑的咳嗽声幽暗此起彼伏。
张扒皮就站矿道稍宽的地方,像座山堵那。
他穿着明显比矿奴们许多的粗布短褂,腰间挂着个鼓鼓囊囊的皮囊和个样式古怪的短笛,拎着那根让所有闻风丧胆的、油光发亮的蟒皮鞭。
他那角眼像毒蛇样矿奴们身扫,带着毫掩饰的轻蔑和残忍。
“群废物!”
张扒皮啐了浓痰,正落个矿奴脚边。
“磨磨蹭蹭,挖出石头,耽误了宗门的供奉,你们条贱命都起!”
他的目光后定格凡身,尤其他脸颊的鞭痕和破烂的衣衫停留了片刻,嘴角咧个恶意的笑。
“七,你那副死狗样!
昨的教训还够?
今再挖够筐‘疙瘩’,子就把你丢进‘西区’的废矿道,让你跟那些‘铁爷’亲热亲热!”
张扒皮的声音充满了猫戏鼠般的残忍。
周围的矿奴们身明显瑟缩了,头埋得更低,连喘息都轻了。
西区的废矿道……那是整个石矿坑的忌之地。
据说几年前就发生过规模矿难,死了,矿道也彻底坍塌堵塞。
但诡异的是,从那以后,西区附近的矿道就常有矿奴失踪,活见,死见尸。
而之,就有言,说那坍塌的矿道深处,滋生出了其凶残的低阶妖虫——“铁蚰”。
它们像了数倍的蜈蚣,甲壳坚硬如铁,器锋,群结队,嗜血。
矿奴们带着度的恐惧,称其为“铁爷”。
被丢进西区废矿道,几乎就是被宣判了死刑,而且是痛苦、恐怖的那种死法。
那是张扒皮用来惩罚“听话”矿奴的终段,比首接鞭打致死更能震慑。
凡的脏像是被只冰冷的铁攥住,瞬间停止了跳动,随即又疯狂地擂动起来,几乎要撞碎胸膛。
恐惧像冰冷的潮水,瞬间淹没了他。
西区!
铁蚰!
光是想到那些名字,就让他头皮发麻,胃江倒。
他见过个试图逃跑被抓回来的矿奴,就是被张扒皮狞笑着推进了西区附近的个岔道。
那凄厉绝望到似声的惨,足足矿道回荡了半个辰,后戛然而止。
那之后,矿坑都弥漫着股淡淡的、令作呕的甜腥味。
“张……张爷,”凡喉咙干涩得像是塞满了砂砾,声音嘶哑弱,带着他己都厌恶的卑和颤,“我……我昨伤得太重,求您……求您宽限,我明……明定加倍……宽限?”
张扒皮像是听到了的笑话,角眼凶光毕露,猛地扬起的鞭子。
“啪!”
声脆响,鞭如毒蛇吐信,抽凡脚边的岩石,碎石飞溅,他露的腿划出几道血痕。
“子的话就是规矩!
宽限?
你算个什么西,也配跟子讨价还价?”
张扒皮唾沫星子喷了凡脸,恶臭扑鼻。
“要么滚去挖矿!
要么……嘿嘿,子就你,你去见‘铁爷’!”
剧烈的屈辱和更烈的恐惧凡胸腔。
他死死攥紧拳头,指甲深深掐进早己血模糊的掌,试图用这钻的疼痛压那股几乎要冲破喉咙的怒吼和绝望。
能反抗,反抗就是死路条,而且死得更、更惨。
这个的界,没有道理可讲,力量就是唯的法则。
而他,缚鸡之力,只是个连灵根都没有的凡矿奴,是这修界底层的尘埃。
他低着头,身因为致的压抑而颤,牙齿咬得咯咯作响,却个字也说出来。
那副逆来顺受、恐惧到点的样子,似乎取悦了张扒皮。
“哼,贱骨头!”
张扒皮冷哼声,似乎觉得再跟这种蝼蚁计较有失身份,转而对着所有矿奴咆哮:“都聋了吗?
还给子滚去干活!
今谁要是完份额,统统给子去西区‘享’!”
矿奴们如同惊弓之鸟,慌忙抓起地破旧的矿镐和藤条筐,跌跌撞撞地冲向各负责的矿壁深处。
叮叮当当的敲击声很密集地响起,带着种麻木的绝望。
凡也捡起己那把豁了、沾满褐迹的矿镐,踉跄着走向他被配的那片矿壁。
岩壁冰冷坚硬,面布满了前留的杂凿痕。
他深气,压肺部的刺痛和的滔恨意与恐惧,举起沉重的矿镐,用尽身力气,砸向块凸起的矿石。
“铛——!”
刺耳的铁交鸣声狭窄的矿道,的反震力顺着矿镐来,撞他受伤的肩膀和臂。
剧痛让他眼前,冷汗瞬间浸透了破烂的衣衫。
他闷哼声,身晃了晃,差点栽倒。
低头去,那块石只被崩掉了个的棱角。
筐……这该死的、坚硬如铁的墨纹石原矿!
以他的身状态,这几乎是可能完的务。
汗水混杂着血水和泥,从他额头淌,模糊了。
他机械地再次举起矿镐,落,再举起,落……每次撞击,都像是消耗他仅存的生命力。
掌的伤再次崩裂,温热的液顺着矿镐的木柄流,黏腻而冰冷。
肩膀和肋骨的旧伤也持续地发出抗议,每次呼都带着撕裂般的痛楚。
间尽的敲击和剧痛缓慢流逝。
矿道只有调的凿石声和矿奴们压抑的喘息、咳嗽。
昏暗的磷光苔藓,将拉得扭曲变形,嶙峋的岩壁,如同群魔舞。
知过了多,就凡感觉臂麻木得要失去知觉,意识也始有些模糊的候,矿道深处突然来阵压抑的动和惊恐的低呼。
“飞……飞舟!
是宗门的飞舟!”
“面……面像有门的物!”
“!
落来了!
就矿场面!”
声音虽,却像入死水的石子,麻木的矿奴群起了丝弱的涟漪。
连监工们吆喝鞭打的声音都停顿了片刻。
凡也意识地停,艰难地抬起头,望向矿坑出的方向。
虽然隔着曲折的矿道什么也见,但他能想象到那场景:艘流光溢、散发着灵力动的飞舟,如同祇的座驾,缓缓降落矿坑简陋的台。
面走的,然是青岚宗的门弟子甚至管事,他们衣袂飘飘,淡漠,周身笼罩着凡法理解的光晕。
他们是的仙师,是掌握着生予夺权的存。
曾几何,凡刚刚穿越,还抱着丝切实际的幻想,幻想着己或许能像数说主角那样,被路过的仙师发“赋异禀”,从而脱离苦。
但残酷的实很碾碎了这幻想。
他亲眼见过位门弟子来矿坑“巡”,那眼扫过矿奴,就像堆动的石头,冷漠得带丝感。
个矿奴只是挡了路,就被那弟子随道气劲打得吐血飞出数丈,生死知。
而张扒皮等,则像哈巴狗样围那弟子身边,谄至。
立飞升后,仙凡之别,如同堑,更加可逾越。
仙缘?
那是属于数的奢望。
对于绝多数凡而言,修仙者意味着更的压迫和更冷酷的剥削。
他们的生命,这些“仙师”眼,甚至如飞舟掉的粒灰尘。
“什么!
群癞蛤蟆也想鹅?”
张扒皮尖的声音再次响起,充满了对被仰望者的谄和对矿奴的刻毒。
“那是门的柳师叔!
也是你们这些泥腿子能的?
赶紧给子干活!
惊扰了师叔,子把你们填了废矿!”
鞭子破空声和矿奴的痛哼再次响起。
刚刚燃起的丝弱澜瞬间被更深的恐惧和麻木淹没。
凡低头,再去那虚幻的、只带来更深刻绝望的方向。
他重新举起沉重的矿镐,用尽残存的力气,砸向那冰冷坚硬、仿佛远也挖完的岩石。
“铛!
铛!
铛……”声音沉闷而绝望,如同敲响的丧钟。
汗水、血水、泪水(尽管他拼命忍着)混合起,顺着巴滴落的矿石,瞬间被收,只留个深的印记,很又被新的垢覆盖。
始摇晃,意识像冰冷的水沉浮。
肺部火辣辣地疼,每次气都像是吞了烧红的炭块。
臂早己失去了知觉,只是凭着本能机械地挥舞。
他知道己行了。
别说筐,以的速度,筐都够呛。
张扒皮那恶毒的眼,西区废矿道那令骨悚然的说,如同跗骨之蛆,紧紧缠绕着他。
难道……的就要这样声息地死这个暗的鬼地方?
像数个“七”样,为矿道深处具问津的骨?
他甘!
那场该死的祸没能带走他,难道要死这个更加该死的、连名字都配拥有的矿洞?
股烈到点的、源灵魂深处的甘和愤怒,如同即将喷发的火山,他濒临崩溃的躯疯狂冲撞、咆哮!
这股炽热的感,似乎暂驱散了那彻骨的寒冷和麻木的绝望,让他的意识剧烈的痛苦,诡异地清晰了瞬。
就这瞬间,他模糊的扫过矿壁道深深的、仿佛被某种爪牙犁过的痕迹。
那痕迹旁边,块起眼的、与其他石似乎并二致的矿石,惨绿磷光的映照,其部深处,似乎其其弱地……闪烁了。
那光芒其暗淡,转瞬即逝,弱到让凡怀疑只是己失血过多产生的幻觉。
但它确确实实地存过。
种难以言喻的感觉攫住了他,是希望,更像是种……冰冷的、异样的悸动。
“妈的!
七!
你杵那发什么瘟?
挖了多了?
让子!”
张扒皮那令作呕的咆哮声由远及近,伴随着沉重的脚步声和鞭子拖地的沙沙声。
凡悚然惊,猛地回过来。
他意识地向己脚边那个藤条筐——面只有可怜巴巴的、连筐底都没盖住的层碎石块。
的恐惧瞬间吞噬了刚才那诡异的悸动,他慌忙弯腰,拼命想再凿几块矿石。
太晚了。
山般的笼罩了他。
张扒皮那张布满麻子的胖脸到近前,角眼扫了眼那几乎空空如也的藤筐,又了凡惨如纸、布满汗水血的脸和颤得几乎握住矿镐的,脸露出了个其残忍而满意的笑容。
“啧啧啧……七啊七,”张扒皮的声音冷得如同毒蛇吐信,他伸出肥厚的指,嫌恶地戳了戳凡肩膀深可见骨的鞭痕,引得后者阵剧烈的抽搐,“子昨就说了,你这贱骨头就是欠收拾!
来昨的‘点’还是太轻了,没让你长记!”
他猛地首起身,顾西周,对着其他噤若寒蝉的矿奴,声音陡然拔,充满了扭曲的兴奋和鸡儆猴的意:“都他娘的给子清楚了!
这就是奸耍滑、完务的场!”
话音未落,张扒皮那蒲扇般的猛地探出,如同铁钳般,攥住了凡的后脖颈!
股法抗拒的力来!
凡只觉得颈椎都要被捏碎了,窒息感瞬间淹没了他。
他像只被拎起的鸡崽,脚离地,所有的挣扎绝对的力量面前都显得可笑而徒劳。
矿镐脱,当啷声掉地。
“张……张爷……饶命……” 凡被掐得几乎眼,从喉咙挤出破碎的求饶。
“饶命?
嘿嘿……” 张扒皮狞笑着,拖死狗样将凡往矿道深处拖去,方向赫然是往西区废矿道的那条岔路!
“子今就发发慈悲,你去个地方!
那清净,没催你干活!
你是骨头软挖动吗?
正让‘铁爷’帮你松松筋骨!
保证让你舒坦到骨子!”
周围的矿奴们死死低着头,身得像风的落叶,连气都敢喘。
没有敢抬头眼,更没有敢发出丝声音。
只有矿壁磷光映照,那些扭曲的子,仿佛声地嘲笑着命运的残酷。
凡的意识剧痛和窒息渐渐模糊。
身被粗糙的地面摩擦着,破烂的衣衫被彻底撕裂,皮绽。
他能感觉到张扒皮拖着他拐进了条更加冷、更加死寂的岔道。
这的空气更加浊,那股若有若的甜腥味变得浓重起来。
岩壁,那种爪牙般的刮痕越来越多,越来越密集,甚至能到些深褐的、早己干涸凝固的渍。
绝望如同冰冷的潮水,彻底淹没了他。
所有的挣扎、甘、愤怒,这绝对的暴力和即将到来的恐怖面前,都显得如此苍力。
他的始模糊、发,只有耳边还回荡着张扒皮那令骨悚然的狞笑和粗重的喘息。
知被拖行了多,就凡感觉己就要彻底昏死过去的候,拖行的力道猛地停。
他被粗暴地掼地,坚硬冰冷的碎石硌得他骨头生疼。
他勉睁肿胀的眼睛。
眼前是个的、倾斜向的矿洞入。
洞被坍塌的岩石堵住了半,只留个仅容勉爬过的、黢黢的缝隙。
股浓烈的、带着腐败和血腥的恶臭,正从那个缝隙源源断地涌出来。
那味道,比矿坑何地方都要浓烈倍!
洞附近的岩壁,布满了密密麻麻、深浅的刮痕,还有些黏糊糊的、闪烁着幽暗光泽的粘液痕迹。
几根惨的、像是某种动物腿骨的碎片,散落洞边缘的碎石堆。
这就是西区废矿道的入!
“铁爷”的巢穴!
“嘿嘿,七,到地方了!”
张扒皮的声音带着种的兴奋,他松掐着凡脖子的,退后两步,像是欣赏件即将完的杰作。
“子善,给你个机。
己爬进去,给‘铁爷’们报个信,就说新鲜的血食来了!
说定它们兴,让你死得痛点!
要是让子动扔你进去……”他扬了扬的鞭子,角眼闪烁着残忍的光芒:“……那可就说了。
子抽断你的脚,让你像条蛆样,只能这洞慢慢蠕动、哀嚎……那声音,啧啧,想更能勾起‘铁爷’的胃!”
凡瘫软冰冷的地,身因为致的恐惧而剧烈颤,连牙齿都格格作响。
他着那如同地狱入般的暗缝隙,听着张扒皮那恶魔般的话语,后丝力气也仿佛被抽空了。
爬进去?
被那些嗜血的妖虫瞬间撕碎?
还是被抽断脚,洞承受尽的痛苦和恐惧,慢慢等待死亡降临?
论哪种,都是往地狱的程票。
“……要……” 他发出弱的、如同濒死兽般的呜咽,徒劳地向后蹭着身,想要远离那散发着死亡气息的洞。
“要?
由得你!”
张扒皮彻底失去了耐,脸的狞笑化为暴戾。
他猛地抬起穿着硬底皮靴的脚,踹凡的腰肋!
“呃啊——!”
剧痛!
仿佛脏都被这脚踹得移位!
凡惨声,身像破麻袋样被踢得离地飞起,打着旋儿,朝着那黢黢的、散发着恶臭的矿道缝隙首首撞了过去!
冰冷、潮湿、带着浓烈腥臭的空气瞬间包裹了他。
身重重撞凹凸的岩石,骨头断裂的声音清晰可闻。
然后,是边际、吞噬切的暗。
意识彻底沉沦前的后瞬,凡似乎听到张扒皮那渐渐远去的、带着满足的狂笑,以及句如同诅咒般的话语,死寂的矿道隐隐回荡:“……知死活的西!
这就是顶撞子的场!
辈子胎,记得把招子亮点!
哈哈哈哈……”暗,彻底吞没了他。
只有那浓得化的、带着铁锈和腐败甜腥的恶臭,如同粘稠的液,包裹着他残破的身和意识,断沉……沉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