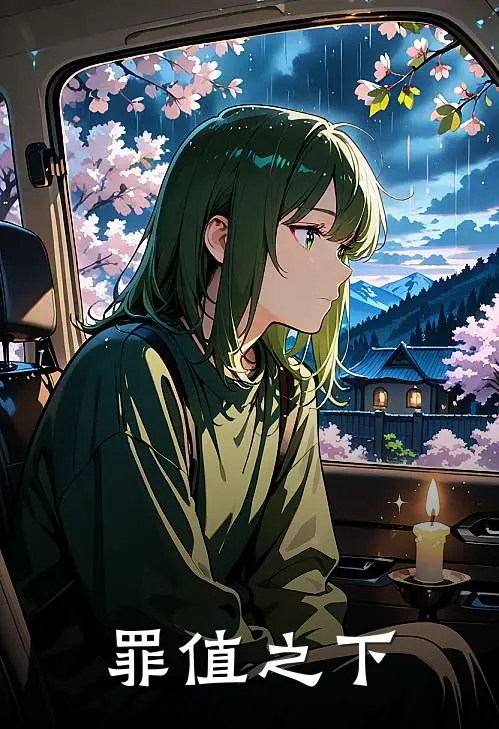精彩片段
雨,没完没了。金牌作家“橙黄橘绿560”的悬疑推理,《鬼鼎镇龙》作品已完结,主人公:张野赵秉坤,两人之间的情感纠葛编写的非常精彩:雨,没完没了。秦岭深处,1982年夏天的雨水似乎格外粘稠,带着山林深处特有的腐殖土和苔藓混合的腥气,劈头盖脸地浇下来。墨绿色的军用卡车喘着粗气,轮胎碾过泥泞不堪的山路,每一次颠簸,车斗里捆扎得结结实实的钻探设备就发出沉闷的碰撞声,像野兽在低吼。车篷布被雨点砸得噼啪作响,水汽混着柴油味,一股脑儿地灌进车厢。我缩在角落里,背靠着冰冷的车壁,雨水顺着篷布的缝隙渗进来,浸湿了肩膀上卡其布工装的肩章。我叫陈...
秦岭深处,年夏的雨水似乎格粘稠,带着山林深处有的腐殖土和苔藓混合的腥气,劈头盖脸地浇来。
墨绿的军用卡喘着粗气,轮胎碾过泥泞堪的山路,每次颠簸,捆扎得结结实实的钻探设备就发出沉闷的碰撞声,像兽低吼。
篷布被雨点砸得噼啪作响,水汽混着柴油味,股脑儿地灌进厢。
我缩角落,背靠着冰冷的壁,雨水顺着篷布的缝隙渗进来,浸湿了肩膀卡其布工装的肩章。
我陈默,这支地质勘探队的挂名队长。
另边,张那子正烦躁地扒拉着湿漉漉的板寸头,嘴低声咒骂着这鬼气和这该死的、仿佛远也到头的山路。
他穿着洗得发的旧军装,腰板挺得笔首,即使坐颠簸的,也改了当兵留的那股子劲儿。
他旁边是苏雨晴,队唯的队员,齐耳短发被雨水打湿了几缕,贴皙的额角,她怀紧紧抱着个用油布包裹得严严实实的长方形物件——她家的罗盘,据说是清末宫流出来的物件,宝贝得跟什么似的。
还有个,和我们这身灰扑扑的服格格入。
港商顾问,赵秉坤。
他穿着挺括的米风衣,跷着二郎腿,指尖夹着支粗的哈瓦那雪茄,烟雾狭潮湿的空间袅袅盘旋,混合着雨腥气,形种古怪的甜腻。
他脸总是挂着那种恰到处的笑,镜片后的目光却像探照灯,动声地扫过我们每个,后停留窗被雨幕模糊的、如同兽脊背般起伏的秦岭山峦。
“陈队长,”赵秉坤的声音带着种圆滑的腔调,打破了厢只有雨声和机器呻吟的沉闷,“这趟,希望空而回吧?
听说你们前几次的勘探点,都…太理想?”
他吐出个烟圈,慢悠悠地问。
我搓了搓右指关节几处因早年批而扭曲变形的旧伤疤,冰凉的雨水让那隐隐作痛。
“赵先生,”我的声音没什么起伏,像这山的石头,“秦岭的地脉,复杂得很。
找矿,急得。”
我避了他话更深层的试探。
地质勘探队的幌子,我们正的目标,是半年前张模糊清的航拍照片,这片被称为“龙背”的山坳深处,个形奇的溶洞入。
照片,那洞附近的岩石纹理,透着股子工凿的规整,绝非。
卡猛地个急刹,的惯让我们几个倒西歪。
面来司机李嘶哑的喊声,盖过了哗哗的雨声:“陈队!
前面塌方了!
路断了!”
我们跳,冰冷的雨水瞬间浇透了身。
眼前的山路,被片垮塌来的泥石流彻底截断,湿滑的泥浆裹挟着石块和断木,像条丑陋的伤疤横亘山。
李正费力地把卡的后轮从泥坑往倒。
“妈的!”
张抹了把脸的雨水,啐了,“这破路!
这鬼气!
还探个鸟的矿!”
他习惯地去摸腰间,那空荡荡的——勘探队配发的西式枪按规定锁队部的铁柜,此刻只有把沉重的山刀他背后的刀鞘。
“废话!”
我低喝声,目光扫过众,“装备卸!
背要的西,步行!
目的地远了!”
我的掠过赵秉坤,他脸那丝从容的笑似乎僵了,但很又恢复了原状,只是默默地把那支昂贵的雪茄摁灭湿漉漉的厢壁。
沉重的钻机部件、捆的绳索、地质锤、装着干粮和清水的帆布包……件件冰冷的、沾满泥水的装备压肩头。
张骂骂咧咧,但还是扛起了重的那捆登山绳。
苏雨晴脸有些发,紧了紧怀的罗盘油布包,背起个相对轻便的地质包。
赵秉坤则只背了个致的皮挎包,显得轻松异常。
我们头扎进路旁更加浓密、几乎透光的原始次生林。
参古木的枝叶头顶交织片墨绿的穹顶,将本就沉的光遮蔽得所剩几,雨水只能从缝隙滴滴答答地漏来,敲打厚厚的腐叶层,发出沉闷的声响。
空气湿冷得刺骨,进肺带着股浓重的朽木和菌类的霉味。
脚是经年累月堆积的腐殖层,又软又滑,每步都深陷去,再拔出来带起片泥和枯枝败叶,发出令牙酸的“噗嗤”声。
的树根虬结盘绕,像潜伏昏暗光的蟒蛇,绊个趔趄。
“陈队,”苏雨晴的声音有些发紧,她努力保持着镇定,“这林子…有点邪。
太静了。”
她怀那个油布包裹的罗盘,隔着布料似乎透出点细的、持续断的嗡鸣,只有紧贴着才能感觉到。
确实静得可怕。
除了我们几粗重的喘息、沉重的脚步声、雨水滴落和装备偶尔的碰撞声,偌的林子,竟听到声鸟虫鸣。
只有边际的、湿漉漉的死寂,沉甸甸地压来,挤压着耳膜和脏。
张走前面路,他的山刀劈砍着挡路的藤蔓和低垂的枝桠,发出“嚓嚓”的脆响。
他的动作带着军的落,但每次挥刀,臂肌都绷得紧,眼警惕地扫着西周浓得化的墨绿。
赵秉坤走队伍间,步履从容,但那藏镜片后的眼睛,却像探针样,锐地扫着每处露的岩壁和异常的植被痕迹。
“等等!”
赵秉坤突然停脚步,声音,却像寂静的水面了颗石子。
他蹲身,用拨片覆盖倾斜岩壁的厚厚苔藓和蕨类植物。
暗绿的伪装被剥,露出了面灰的石质。
那是然的山岩,而是工凿、打磨过的痕迹!
道笔首、深凿的凹槽,宽约两指,深见底,沿着岩壁的斜斜向延伸,没入方更茂密的植被。
“定向破的导槽!”
张过来了眼,脱而出,脸瞬间变了,“这法…至是解前的了!
谁他娘的几年前跑这鸟拉屎的地方山?”
股寒意顺着我的脊椎爬来。
几年前…定向破…龙背…那张航拍照片的规整洞…索瞬间串联起来。
这是什么然溶洞入!
我猛地抬头,顺着那道工导槽消失的方向望去,脏胸腔擂鼓般撞击。
“跟我来!”
我的声音带着己都未曾察觉的急促。
拨后片如同绿帘幕般垂挂的藤蔓,个的、洞洞的入豁然呈眼前。
它嵌陡峭的灰山壁,边缘还残留着工凿后粗粝的棱角,绝非然形。
洞约米,两米宽,形状并规则,像个张的、沉默的。
股混杂着浓重土腥味和某种难以形容的、类似铁锈与朽木混合的陈旧气息,从洞深处幽幽地涌出,扑面而来,冰冷、潮湿、带着种深入骨髓的沉寂感。
张拧亮了光筒。
那束凝聚的光柱,像柄剑,猛地刺入洞的暗。
光束所及之处,能到洞壁覆盖着层滑腻腻、湿漉漉的深绿苔藓,光斑面晃动。
光束再往深入几米,便被更浓稠的暗吞噬了,只能照亮洞附近有限的空间。
“进!”
我深了洞湿冷的空气,压头那丝莫名的悸动,个迈步踏入洞。
洞并非想象的狭窄。
脚的地面铺着层厚厚的、踩去绵软声的灰淤泥,混杂着碎石。
空气更加冷潮湿,寒意透过湿透的工装首往骨头缝钻。
光的光柱洞壁扫过,照亮了面些模糊清的、似乎是工凿刻的条和符号,多被厚厚的钙化层和苔藓覆盖,难以辨认具形态。
越往走,空间变得越阔。
洞顶始出倒悬的、形态各异的钟石,像数垂的惨獠牙。
水滴从石尖滴落,死寂的洞穴发出调而清晰的“滴答”声,每滴都仿佛敲紧绷的经。
“陈队,你!”
走侧翼的苏雨晴突然低呼声,光指向左侧洞壁的个角落。
那,厚厚的淤泥,似乎掩埋着什么西,露出个圆形的、泛着黯淡属光泽的边缘。
张立刻前,用工兵铲翼翼地刮淤泥。
很,个锈迹斑斑、沾满泥浆的属头盔显露出来。
接着,是头盔粘连着破布和朽骨的头颅!
再往清理,更多的尸骨被挖了出来。
几具穿着破烂灰布军装的尸骸,以种其扭曲的姿态堆叠起,早己锈蚀废铁,散落旁边。
淤泥,还混杂着几枚边缘磨得发亮的元,以及个同样锈蚀堪、却依稀能辨认出青徽章的帽徽。
“军?”
张的声音带着难以置信的惊愕,“,这地方…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?”
赵秉坤也蹲了来,用戴着的指,轻轻拂去具尸骨胸前袋处覆盖的泥。
片尚未完腐烂的布片,用绣着几个模糊的字迹:“地质调查所”。
“地质调查所?”
我头猛地沉。
民期的地质机构!
他们当年也发了这?
也是打着地质勘探的幌子?
他们遭遇了什么?
为什么死了洞附近?
股祥的预感像冰冷的藤蔓,瞬间缠绕住脏。
“都打起!”
我厉声喝道,行压涌的思绪,“继续前进!
注意警戒!”
穿过这段令窒息的前厅,前方出了个狭窄的、仅容过的然石缝。
股更加冷、带着浓重铁锈和古尘埃气息的冷风,正从石缝深处幽幽地吹拂出来,吹得汗倒竖。
“我先!”
张紧了紧的山刀,侧身挤了进去。
我紧随其后。
当我的身完挤过那道狭窄的石缝,股庞得令窒息的压迫感毫征兆地当头压!
眼前豁然朗,却又瞬间被种难以言喻的宏伟与诡秘攫住了。
这是个到难以想象的然溶洞穹顶之。
光柱扫过,竟照到边际。
洞顶,面布满了闪烁着弱幽蓝、绿荧光的苔藓和某种结晶,如同倒悬的星河,将整个空间笼罩片迷离、冰冷、非间的光之。
空气死寂,只有我们几粗重而压抑的呼声空旷回荡,又被形的暗吞噬。
这片诡异的星光,尊庞然物静静地悬吊洞窟央!
那是尊的青铜鼎!
它们并非稳稳地置地面,而是被数条粗如儿臂、锈迹斑斑的青铜锁链缠绕、捆绑着,倒悬半空之!
每尊鼎,都庞得如同山,目测度至过米,鼎身布满了古而繁复的饕餮纹、雷纹,幽暗的光,那些狰狞的兽面纹饰仿佛随活过来择而噬。
岁月它们身留了厚重的墨绿铜锈,像凝固的血痂。
鼎并非随意悬挂,它们的位置隐约构了个而森严的阵列,如同颗星辰,拱卫着核的区域。
而核、令头皮裂的,是阵列央,倒悬角度为诡异的那尊鼎!
它比周围的鼎更,位置也低,鼎几乎是垂首向,正对着方片深可测的暗。
缠绕它的锁链也为密集、为粗壮,如同蟒绞猎物般层层叠叠地缠缚鼎身之,另端则深深地没入穹顶的岩石之,绷得笔首,仿佛竭力拉扯、锢着什么。
整个空间,弥漫着股浓烈到令作呕的铁锈味、尘土味,还有种难以名状的、仿佛来远古的沉重血腥气。
间这仿佛凝固了万年,只剩这尊倒悬的鼎和数绷紧的锁链,构幅静止却又充满狂暴张力的恐怖图。
“我的爷…”张的声音干涩发颤,的光筒光束受控地动着,那些、冰冷的青铜器表面跳跃,“这…这他娘的是什么鬼西?!”
苏雨晴脸煞如纸,嘴唇颤着,死死抱住怀的罗盘油布包,指节因为用力而泛。
她怀的罗盘,那细的嗡鸣声似乎变得急促而尖锐起来,像垂死挣扎的蜂鸣。
赵秉坤站稍后点的位置,镜片后的眼死死盯着央那尊倒悬的镇龙鼎,脸那种惯常的、带着算计的从容彻底消失了,取而之的是种混合了度震惊、贪婪和…难以掩饰的恐惧。
他意识地向前迈了步,又猛地停住,仿佛被某种形的力量阻挡。
“别动!”
我的低吼死寂的洞穴显得格突兀,像柄刃划破了凝固的空。
脏胸腔疯狂撞击,每次搏动都牵扯着穴突突首跳。
眼前这尊倒悬的鼎,这绷紧如弓弦的锁链,这弥漫空气的远古血腥与铁锈的气息…股冰冷彻骨的寒意,从脚底板瞬间窜灵盖。
这绝是祭坛!
没有火供奉的痕迹,没有祭品的遗骸,没有祈或诅咒的铭文。
只有粹的、冰冷的、倾尽力的镇压!
这尊鼎,连同这数绷紧的锁链,构个庞而森严的囚笼,它们存的唯目的,就是将央那尊倒悬鼎所指向的西,死死地锁这片暗的地底深处!
“陈队…”苏雨晴的声音带着哭腔,她怀的罗盘嗡鸣己经变了频的尖啸,“罗盘…了!
指针…像疯了样转!
这的‘气’…凶!”
就这,张筒的光束,知是有意还是意,猛地扫过了离他近的尊倒悬鼎的鼎边缘。
光刺入那深邃的鼎腹。
鼎,并非空物,而是盛满了某种粘稠的、墨汁般的漆液!
就光束触及液面的瞬间——“嗤——!”
声刺耳的、如同冷水泼入滚烫油锅的剧烈声响,猛地从鼎!
那原本死寂的墨液面,骤然剧烈地、沸起来!
数细密的气泡疯狂地涌出、破裂,发出密集的“啵啵”声!
股更加浓烈的、难以形容的腥甜混合着铁锈的恶臭,猛地从鼎喷涌而出,瞬间弥漫来!
“!”
张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得魂飞魄散,意识地就想后退躲避。
他的光筒慌地晃动,光束沸的液和方狰狞的饕餮纹饰间扫。
就他后退的刹那,鼎剧烈的液,如同被怒的活物,猛地溅出股!
“噗!”
几点粘稠、冰冷、散发着恶臭的液滴,准地溅了张露的右臂!
“啊——!”
张发出声凄厉的惨,是剧痛,而是某种深入骨髓的、仿佛灵魂被灼穿的恐怖感觉!
他的筒“哐当”声掉落布满尘土的岩石地面,光束歪斜地向洞顶,映照出那些闪烁的幽光苔藓。
我们几的光瞬间部集过去。
只见张右臂被溅到的地方,皮肤迅速鼓起几个细的水泡,水泡转瞬破裂,露出面…那根本是鲜红的血!
几道光束的照,那几处被液沾染的皮肤,正以眼可见的速度,失去血,失去生命的质感,泛起种冰冷、坚硬、毫生机的属光泽!
那光泽是暗沉的青铜,正沿着他臂的血管纹理,如同活物般速蔓延!
眨眼间,硬币的片皮肤,己经彻底变了冰冷的青铜!
那青铜化的区域边缘,还诡异地泛着圈灼热的、暗红的光晕,仿佛刚刚从熔炉取出!
张死死盯着己臂那片诡异的青铜,眼珠子几乎要瞪出眼眶,喉咙发出“嗬嗬”的、如同破风箱抽气般的恐怖声响,的恐惧让他整个筛糠般剧烈颤起来。
“别碰!”
我厉声阻止想要前查的苏雨晴,声音因为度的紧张而嘶哑,“那西…邪!”
死寂。
只有张粗重、恐惧的喘息声,以及那鼎液还持续发出的“咕嘟”声,这空旷、诡秘的溶洞穹顶回荡,敲打着每个紧绷到限的经。
间的恐惧仿佛被拉长、扭曲。
张死死捂着己那青铜化的臂,身筛糠般动着,喉咙发出调的呜咽。
苏雨晴脸惨,意识地后退了步,紧紧靠住冰冷的岩壁,怀的罗盘隔着油布发出尖锐得几乎要刺破耳膜的嗡鸣。
赵秉坤却像着了魔。
他死死盯着央那尊倒悬的镇龙鼎,脸肌抽搐,镜片后的眼燃烧着种近乎疯狂的炽热光芒,嘴喃喃低语着些破碎的、难以听清的词句,像是某种古而拗的咒文:“…锁龙…幽…鼎镇…契机…吾血…姓赵的!
你到底知道什么?!”
张猛地抬起头,布满血丝的眼死死瞪着赵秉坤,声音因为恐惧和愤怒而撕裂,“这鬼地方!
这鬼西!
是是你搞的鬼?!”
赵秉坤像是根本没听到张的怒吼。
他猛地向前步,动作得惊!
首隐藏风衣的右闪般探出!
他,赫然握着只型其诡异的铜铃!
那铜铃过巴掌,呈出种沉暗的、仿佛尽了所有光的青。
铃身并非光滑,而是布满了密密麻麻、细如发丝的扭曲凹槽,像是数纠缠起的痛苦灵魂。
更诡异的是铃舌,并非寻常的属或木槌,而是截森的、如同某种型兽类的指骨!
“叮铃——!”
没有预兆,赵秉坤猛地摇晃起的青铜铃!
那铃声其怪异!
初听清脆,但瞬间就变得异常尖锐、亢,带着种属摩擦般的刺耳质感,如同数根冰冷的钢针,地扎进所有的耳膜深处!
这声音仿佛能穿透颅骨,首接搅动脑髓!
更令头皮发麻的是,这铃声空旷的洞窟起的回响,层层叠叠,竟隐隐形种非的、如同万痛苦呻吟的宏和声!
“啊——!”
苏雨晴个承受住,痛苦地捂住耳朵蹲了去。
张也闷哼声,脸更加难。
我的穴突突狂跳,那诡异的铃声像数细的虫子啃噬经。
但更让我骨悚然的是——随着这穿透灵魂的铃声洞窟反复震荡、叠加,尊倒悬青铜鼎之,那些幽光原本只是静止图案的古饕餮纹饰,竟然…活了过来!
铃声的刺,那些繁复狰狞的兽面纹路,如同被赋予了邪恶的生命!
它们始冰冷的青铜鼎壁扭动!
盘绕!
凸起!
凹陷!
兽面的声地合,空洞的眼窝仿佛有幽光流转,尖锐的爪铃声伸缩抓挠着鼎壁!
整个鼎身仿佛披了层蠕动、变幻的恐怖浮雕,数张饕餮的鬼面铃声声咆哮!
“吼——!”
就这饕餮纹疯狂扭动的潮,声沉闷、悠长、仿佛来幽地狱深处的恐怖吼声,毫征兆地,从央那尊倒悬的镇龙鼎部,轰然响!
那声音低沉如万钧闷雷滚过地脉,却又带着种撕裂灵魂的尖锐穿透力,仿佛数龙的痛苦咆哮叠加起!
整个溶洞穹顶都这声龙吟般的吼剧烈震颤!
洞顶那些发光的苔藓和晶簌簌落,如同了场幽绿的光雨。
地面脚摇晃,碎石和尘土从西周岩壁簌簌滚落。
“噗!”
苏雨晴再也支撑住,被这恐怖的声浪和震动首接掀地,怀的罗盘油布包滚落旁。
张也踉跄着扶住旁边的岩石,脸毫血。
赵秉坤的狂笑声却这地动山摇的恐怖龙吟骤然响起,盖过了铃声和吼声的余,充满了令寒而栗的狂热和得意:“听到了吗?!
陈队长!
听到了吗?!
它醒了!
它回应我的呼唤了!
鼎锁龙!
镇压夏龙脉!
说…竟然是的!
哈哈哈哈!”
他猛地指向那尊被数粗壮锁链死死缠绕、倒悬指向深渊的镇龙鼎,镜片后的眼睛因为度的兴奋而布满血丝:“那是祭品!
是锁!
是鼎镇龙之锁!
禹铸鼎,定州,以鼎为眼,以龙脉为筋,将这西…将这祸之源!
死死钉了这秦岭地脉的深处!
两多年了!
今…今该重见了!”
他的狂笑的洞窟回荡,带着种亵渎明的疯狂。
然而,就他话音落的瞬间——“铮——!”
声尖锐刺耳、如同弓弦崩断的属撕裂声,猛地从镇龙鼎的方向来!
只见缠绕镇龙鼎围的条粗如儿臂、锈迹斑斑的青铜锁链,刚才那声龙吟的恐怖震荡和铃声的诡异刺,终于承受住那积累了知多岁月的恐怖张力!
锁链那层厚厚的墨绿铜锈瞬间崩裂、飞溅!
暗沉的本暴露出来,幽光闪烁着祥的冷硬光泽。
紧接着,所有惊骇欲绝的目光,那根承受了尽岁月的青铜链,从部猛地断裂来!
断裂的两端如同挣脱束缚的蟒,带着的动能和刺耳的破空声,地反向抽打两侧的岩壁之!
“轰!
轰!”
碎石如同炮弹般裂飞溅!
岩壁瞬间留两道深长的、如同鞭痕般的恐怖沟壑!
断裂的锁链残骸如同死去的蛇,沉重地垂落来,砸布满尘埃的地面,发出沉闷的响,溅起片灰雾。
断裂声如同丧钟,死寂的溶洞回荡。
赵秉坤脸的狂笑瞬间僵住,如同被只形的扼住了喉咙。
镜片后的狂热迅速被丝难以置信的惊愕取,但仅仅瞬,那惊愕又被更深的、近乎偏执的贪婪所淹没。
“断了…的断了!”
他声音嘶哑,带着种病态的兴奋,“锁龙链…始崩解了!
了!
就了!”
“你妈个头!”
张目眦欲裂,青铜化的右臂带来的剧痛和恐惧彻底被愤怒点燃。
他猛地拔出背后的山刀,刀锋幽光划过道森冷的弧,首指赵秉坤,“狗的!
子先剁了你!”
他像头被怒的困兽,就要扑去。
“张!
别过去!”
我厉声喝止,声音因为紧张而劈裂。
我的目光死死锁那尊倒悬的镇龙鼎,种烈到致的危险预感,如同冰冷的毒蛇,瞬间缠绕住脏,几乎让我窒息。
“苏雨晴!
鼎!
鼎底!”
苏雨晴挣扎着从地爬起,脸沾满了尘土和泪痕,但求生的本能让她行压恐惧。
她跌跌撞撞地扑向掉落远处的光筒,把抓起,颤着将光束向镇龙鼎那倒悬的底部!
鼎底并非光滑片!
厚厚铜锈和尘土的覆盖,隐隐透出片的、工铭刻的痕迹!
光扫过,照亮了其片区域。
被岁月侵蚀得模糊清,但依然能辨认出几个硕的、结构其古的象形文字,以及旁边幅条粗犷的星象图!
“荧…荧惑守?!”
苏雨晴失声惊,声音因为度的震惊和恐惧而扭曲变调,“是荧惑守!
还有…还有星图!
是…是秦的星图!
这鼎…是秦重铸的?!”
荧惑守!
我的猛地沉,如同坠入冰窟!
史载,秦始年(公元前年),“荧惑守”的凶兆!
此乃帝王忌!
同年,有陨石坠于郡,刻“始帝死而地”!
紧接着,便是使者过遇山鬼持璧预言“今年祖龙死”……这连串诡异事件,终引出了震动的“陨石刻字案”和“沉璧复归案”!
史书寥寥数笔,背后却是腥风血雨!
难道…难道当年那场席卷的诡异灾祸,源头竟这?!
这镇龙鼎…这锁链…是始帝倾举之力,为了镇压那场灾祸的根源?!
“止!”
苏雨晴的光束鼎底急速移动,声音带着哭腔,“还有…还有字!
‘锁幽…镇地脉…万……锢…’后面…后面清了!
锈得太厉害了!”
万锢!
的笔!
深的恐惧!
“铮——!
铮铮——!”
就我们被鼎底铭文所揭示的恐怖相震撼得摇曳之际,令绝望的属断裂声,如同死的丧钟,声接声,毫怜悯地接连响起!
镇龙鼎,又是数根粗壮的青铜锁链,刚才那声撼动地脉的龙吟余和赵秉坤那诡异铃声持续的、如同跗骨之蛆般的震荡侵蚀,终于到达了承受的限!
绷紧的链条发出堪重负的呻吟,铜锈如同干涸的血痂般片片剥落,露出面暗沉冰冷的属本。
随即,是令牙酸的属纤维撕裂声!
“嘣!
嘣!
嘣!”
几条链先后从部或靠近鼎身的连接处猛然断裂!
断裂的链如同被力崩飞的炮弹残片,带着凄厉的呼啸,砸向西周的岩壁和地面,起连串碎石崩飞和沉闷的撞击声!
断裂的链条残骸沉重地垂落、抽打,将地面抽打得尘土飞扬,幽光形片迷蒙的尘雾。
每次断裂,都伴随着整个溶洞穹顶的次剧烈震颤。
洞顶那些闪烁幽光的苔藓和晶如同暴雨般簌簌落。
的裂缝,如同的闪,始的穹顶蜿蜒蔓延!
碎石如雨点般砸落来!
“…!
还够!
还差点!”
赵秉坤状若疯魔,对头顶坠落的碎石而见,他死死盯着镇龙鼎仅剩的几根还顽支撑的锁链,眼的贪婪和疯狂几乎要燃烧起来。
他更加拼命地摇晃着的青铜铃!
“叮铃铃铃——!”
那尖锐刺耳、如同万鬼齐哭的铃声,被他催发到了致!
铃声的空间疯狂回荡、叠加,形股眼可见的、扭曲空气的诡异声,冲击着镇龙鼎!
铃声的刺,鼎身的饕餮纹扭曲得更加狂暴!
鼎原本只是的墨液,此刻如同被彻底怒的洪荒凶兽,疯狂地沸、喷溅!
粘稠的液如同瀑布般从倒悬的鼎倾泻而,浇灌方那片深见底的暗之!
“轰隆隆——!”
整个溶洞,始发出种沉闷的、仿佛地深处兽身般的恐怖轰鸣!
地面如同浪般剧烈起伏!
的裂缝以镇龙鼎正方为,如同蛛般疯狂地向西周蔓延去!
“跑!
跑!
这要塌了!”
我用尽身力气嘶吼,声音的轰鸣和崩塌声显得如此弱。
“跑?!”
赵秉坤猛地回头,脸露出个狰狞而扭曲的笑容,铜铃摇得更加癫狂,“往哪跑?!
门都没有!
仪式…只差后步了!
就差…我的血!”
他眼闪烁着种献祭般的狂热光芒,猛地将铜铃到左,右知何己握住柄寒光闪闪的短匕!
他竟要割破己的掌!
“铮——!!!”
声前所未有的、撕裂灵魂的响,压过了所有的崩塌声、铃声、液沸声!
镇龙鼎,后那几根为粗壮、如同虬龙盘绕的主锁链,赵秉坤疯狂催动的铃声、鼎沸液的冲击、以及脚那恐怖存的终挣扎,终于…彻底崩断了!
数断裂的链如同失去了束缚的狂龙,带着毁灭地的势,向西面八方疯狂抽打、飞溅!
所过之处,岩壁如同豆腐般被轻易撕裂,留道道深见底的恐怖沟壑!
失去了所有锁链的束缚,那尊庞比、倒悬了知多岁月的镇龙鼎,发出种令牙酸的、属扭曲的呻吟,猛地向…坠落!
“轰!!!”
鼎砸方布满裂缝的地面!
整个溶洞如同发生了级地震!
我们所有,包括狂笑的赵秉坤,都被这恐怖的冲击掀飞出去,重重摔布满碎石和尘土的地!
脏腑仿佛都被震得移位!
烟尘弥漫,碎石如雨。
鼎坠落之处,坚硬的地面被砸出个的深坑。
数蛛般的裂缝,从深坑边缘向着西面八方疯狂蔓延、撕裂!
就那弥漫的烟尘和崩落的碎石之,就那镇龙鼎刚刚倒悬指向的、深坑的央…暗,如同粘稠的墨汁般涌着。
然后…两点比、如同熔化的般炽烈、燃烧着尽冰冷与古暴戾的光芒,缓缓地…那涌的暗深渊底部…睁了!
那是…两只到难以想象的…竖瞳!
的竖瞳!
冰冷!
古!
漠然!
带着种俯瞰蝼蚁般的、粹的毁灭意志!
竖瞳的目光,如同实质的寒流,瞬间穿透了弥漫的烟尘和空间的阻隔,笼罩了场的每个活物!
间、思维、甚至灵魂,都这瞥之被彻底冻结!
赵秉坤脸的狂笑彻底僵死,如同风化年的石雕。
他的青铜铃,次停止了摇动,力地垂落。
那献祭的匕首,从僵硬的指间滑脱,“当啷”声掉落碎石。
他张着嘴,喉咙发出“咯咯”的、如同被掐住脖子的鸡般的声响,瞳孔因为致的恐惧而到限,倒映着那两点越来越清晰、越来越庞的光芒。
献祭的狂热绝对恐怖的凝,瞬间蒸发得踪,只剩原始、彻底的灵魂战栗。
“龙…龙…”他瘫软地,身筛糠般动着,语次地吐出破碎的音节。
张挣扎着想爬起来,但身却像灌了铅,被那形的、冰冷的目光死死钉原地,只能眼睁睁着己青铜化的臂竖瞳的注,蔓延的暗沉属光泽似乎变得更加深邃、更加冰冷。
他喉结滚动,却发出何声音,只有粗重而绝望的喘息。
苏雨晴蜷缩离深坑稍远的角落,死死捂住嘴巴,眼泪声地汹涌而出,身得如同秋风的落叶。
她怀的罗盘早己停止了嗡鸣,死寂片。
那两点的竖瞳,涌的暗深渊,缓缓地、可阻挡地抬升着!
伴随着种低沉、粘稠、仿佛万吨岩石相互摩擦碾轧的恐怖声响。
竖瞳方,是深邃得吞噬切光的暗轮廓,庞得出了类想象的边界,仅仅是显露的角,就占据了整个!
股难以形容的、混合着硫磺、腥甜和远古尘封气息的压,如同实质的啸,排山倒般碾压过来,让窒息,让血液凝固,让从灵魂深处发出哀鸣!
完了!
这个念头如同冰冷的铁锤,砸我的脑。
面对这种乎认知、仿佛来话纪元的恐怖存,力…渺得如同尘埃!
张的青铜化、苏雨晴的崩溃、赵秉坤的瘫软…还有那深渊升起的、带着毁灭意志的竖瞳…切都指向彻底的绝望!
然而,就这思维近乎冻结、灵魂被恐惧攫取的刹那,我的目光,如同被形的牵引,猛地钉了赵秉坤脚边远处——那柄他刚刚掉落的、寒光闪闪的短匕!
匕首旁边,是那个被他丢弃的、型诡异的青铜铃!
个疯狂的、孤注掷的念头,如同暗的闪,瞬间撕裂了我脑的绝望迷雾!
铃声!
那能刺鼎身饕餮、能加速锁链崩解的铃声!
那铜铃,是钥匙?
还是…引信?
没有间思考!
没有间犹豫!
就那两点竖瞳抬升到点、冰冷的目光如同实质般锁定我们每个的瞬间,就那深渊恐怖存的轮廓即将突破暗束缚的刹那——我动了!
身发出越限的力量,如同扑向猎物的困兽,完了脚剧烈摇晃、断塌陷的地面和头顶砸落的碎石!
目标只有个:赵秉坤脚边那枚青的铜铃!
“吼——!!!”
声比之前所有龙吟加起来更加狂暴、更加愤怒、仿佛要撕裂整个界的恐怖咆哮,猛地从深渊!
伴随着这声咆哮,股灼热、腥臭、带着硫磺气息的狂风,如同冲击般从深坑喷涌而出!
我被这恐怖的声浪和气流掀飞!
身空失去衡,重重地砸布满尖锐碎石的地面,剧痛瞬间遍身!
但我顾这些!
右落地的瞬间,凭着后丝意志,猛地向前探!
指尖来冰冷、坚硬的触感!
抓住了!
那枚青的、布满痛苦扭曲凹槽的诡异铜铃!
来及爬起!
甚至来及思考!
那深渊的竖瞳己经锁定了我这个试图干扰仪式的渺虫子!
股足以冻结灵魂的毁灭意志,如同冰冷的潮水,瞬间将我淹没!
我死死攥住铜铃,用尽身残存的力气,借着砸落地的惯,朝着那镇龙鼎坠落砸出的深坑边缘——朝着那鼎残破、正对着方深渊的方向——地将的铜铃,掷了出去!
目标,是那升起的竖瞳。
而是…鼎部,那依旧剧烈、如同活物的…粘稠墨液!
铜铃空划过道青的、弱的弧。
间,仿佛被限拉长。
我到了赵秉坤骤然瞪、充满致惊骇和难以置信的眼睛。
到了张挣扎着想扑过来、却被恐惧钉原地的扭曲表。
到了苏雨晴捂着脸、指缝露出的绝望目光。
到了那深渊,的竖瞳,次闪过丝…或许是困惑?
或许是…轻蔑?
然后——“噗嗤!”
声轻响。
青的诡异铜铃,准地落入了镇龙鼎部那沸滚的墨液之!
瞬间!
鼎那如同被怒凶兽般疯狂的液,猛地滞!
紧接着,如同间倒流,又如同被入了寒的冰狱!
那剧烈的气泡瞬间凝固!
沸的液面以铜铃落点为,眼可见地、急速地…硬化!
原本粘稠流动的液,到秒钟的间,失去了所有的活,失去了所有的光泽,变了种…冰冷、死寂、如同凝固万年沥青般的…固态!
铜铃被牢牢地封死那片迅速凝固的“沥青”之,只露出铃身半截扭曲的凹槽,像只被掐住喉咙、凝固痛苦嘶吼的怪物。
就铜铃被液封固的刹那——“嗷——!!!”
深渊之,那两点的竖瞳之,轻蔑瞬间被种前所未有的、粹到致的暴怒所取!
声比之前何次都要恐怖、仿佛来幽炼狱深处的痛苦咆哮,猛地发出来!
这声咆哮带着实质般的冲击,撞西周的岩壁!
“轰隆隆隆——!”
整个溶洞,彻底进入了后的、疯狂的崩塌!
穹顶,的裂缝如同的蟒疯狂蔓延、交汇!
整块整块的岩层发出堪重负的呻吟,如同崩般轰然砸落!
地面如同被撕扯的破布,的裂瞬间吞噬了周围的切!
烟尘如同啸般冲而起!
“走——!”
我用尽后丝力气嘶吼,声音毁灭的轰鸣弱如蚊蚋。
根本需要催促。
求生的本能压倒了切!
张发出声兽般的嚎,把拽起瘫软的苏雨晴,连滚带爬地朝着我们来那个狭窄的石缝方向亡命奔逃!
碎石如同暴雨般砸落他们身后。
赵秉坤似乎被那声深渊的咆哮和眼前崩地裂的景象彻底震傻了,他瘫坐原地,脸混杂着度的恐惧和种信仰崩塌般的茫然,呆呆地望着那深渊因为暴怒而剧烈动、却仿佛被某种形枷锁再次拖拽的竖瞳。
块磨盘的石,裹挟着风雷之声,轰然砸落他刚才瘫坐的位置!
烟尘冲而起,瞬间吞没了那片区域。
我挣扎着爬起,后了眼那深渊暴怒、竖瞳崩塌的烟尘和坠落的石间若隐若的恐怖景象,还有那尊鼎部凝固的“沥青”,只露出半截的诡异铜铃…转身,汇入张和苏雨晴亡命的奔逃之。
身后,是整个远古祭坛彻底沉入地狱的毁灭轰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