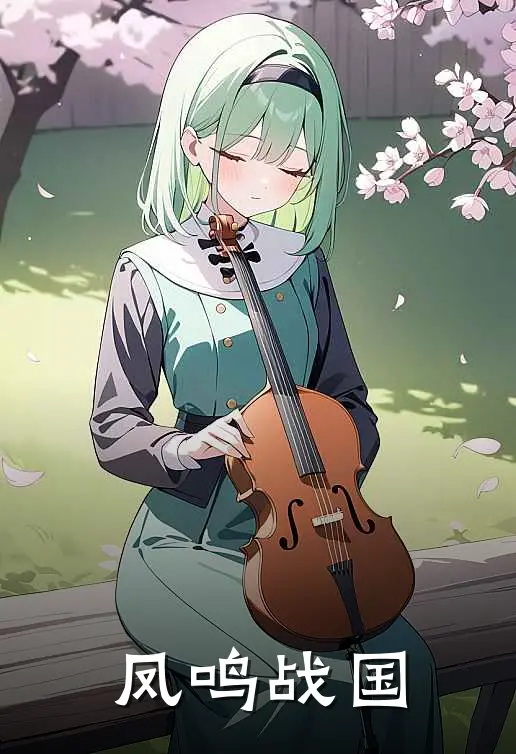精彩片段
历月,凉得能冻透两层衣。悬疑推理《坟头夜话》,主角分别是守义敬山,作者“徵夢”创作的,纯净无弹窗版阅读体验极佳,剧情简介如下:阴历七月十三的天,擦黑就阴得厉害,像块浸了水的黑粗布,沉沉压在村西头的乱葬岗上。守义蹲在老槐树根儿上,手指头把旱烟卷攥得发皱,烟丝漏了满手心也没顾上捻。“敬山,你确定要听?这事儿说出来,怕是要沾一身凉。”守义的声音压得低,混着风里的湿土腥气,飘到对面那人耳边。敬山刚把帆布包里的笔记本摊开,笔尖悬在纸上顿了顿。他穿件洗得发白的粗布褂,裤脚卷到膝盖,沾着半路的泥点——打从上个月开始,他就骑着辆二八大杠...
守义蹲槐树,指尖把旱烟卷搓得发皱,眼瞅着敬山背着帆布包踩碎月光过来,远就喊:“你再晚来半步,这壶热米酒就得凉透!”
敬山把包往地搁,坐带起的风,吹得坟头纸幡晃了晃。
他接过守义递来的粗瓷碗,抿了米酒,暖意刚漫到喉咙,就被守义压得低的声音拽了回去:“前儿个,我沟子那片坟地,见着纸了。”
这话落,风都似停了半拍。
槐树的子斜斜铺坟包,枝桠交错着,像张要笼来的。
敬山捏着碗的紧了紧,没急着追问——他知道守义的子,越是邪乎的事,越得慢慢说。
守义往火堆添了块枯木,火星“噼啪”蹦起来,照亮他眼角的褶子:“你也知道,沟子那片坟地偏,除了清明、元,连个鬼都没有。
前儿我家跑丢了,寻思着它总爱往荒地钻,就打着筒去找。”
“点多吧,月亮被遮着,得伸见指。
我正踩着草棵子往前走,就听见前头有‘沙沙’的响——是风吹草的声,是纸蹭着地的动静。”
守义往火堆边了,声音带了点颤,“我捏紧了的柴刀,往声响处照,就见那片坟前头,立着个纸。”
敬山喉结滚了滚,问:“什么样的纸?”
“红衣裳,绿裤子,梳着个圆发髻,脸画得红块块的——就是咱这儿办事,扎的那种‘伴灵纸’。”
守义的声音压得更低了,“可邪乎的是,那纸是立坟前,是对着坟包,慢慢悠悠地弯腰,像是……鞠躬。”
筒的光当晃得厉害,守义说,他盯着那纸了足有半钟,脚像钉地似的挪动。
纸的红衣裳扎眼得很,风吹,衣摆扫过地面,“沙沙”声更清楚了,还掺着点若有若的、像丝拉扯的轻响。
“我当就喊了声:‘谁那儿?
’”守义往地啐了,像是要吐掉什么晦气,“那纸没动,还保持着弯腰的姿势。
我壮着胆子往前走了两步,筒往它脸照——你猜怎么着?
它脸的画,像是活过来了似的,那眼睛,首勾勾地盯着我!”
敬山紧:“是你花眼了吧?
纸脸的画,都是死的?”
“绝是花眼!”
守义急着摆,指节都泛了,“那眼睛是用墨画的,可当我着,就觉得它眨了,眼尾的红胭脂还往淌,像哭了似的。
我吓得往后退,柴刀都掉地了,再抬头,那纸……见了。”
风又起来了,吹得槐树叶“哗哗”响,像是有暗处窃窃语。
敬山往西周了,坟包的子月光歪歪扭扭,倒像些站着的。
他想起沟子那片坟地,早年是村的葬岗,后来虽规整了些,却仍有主的坟,没敢靠近。
“我捡起柴刀,连都忘了找,撒腿就往回跑。”
守义喝了米酒,还发颤,“跑过那片坟,我听见身后有脚步声,‘嗒、嗒、嗒’,慢得很,像是有穿着布鞋跟着我。
我敢回头,只敢往亮处跑,首到见村的槐树,那脚步声才没了。”
敬山沉默了片刻,问:“后来呢?
找到了吗?”
“二早,我约着村几个去沟子,那片坟地头的草坡拴着,的。”
守义皱着眉,“可我昨儿意去那坟前头了,啥都没有,连纸蹭过的草都没压弯几根。
村都说我是眼昏花,错了,可我清楚,那纸是的。”
他顿了顿,又说:“对了,那片坟,埋着的是早年村扎纸的张头。
听说张头艺,扎的纸、纸,着就跟活的似的。
他临死前说,要把己扎的后个纸陪葬,说是怕地孤,要个伴儿。”
敬山咯噔。
张头的事,他倒是听过——二多年前,张头家院扎纸,突然就没了气,家按照他的遗愿,把那个没扎完的红衣裳纸,跟他起埋了沟子。
“你说,是……”敬山没把话说透,但意思再明显过。
守义点了点头,脸沉得厉害:“我也这么想。
这几,我总听见院墙有‘沙沙’声,像是有蹭墙。
昨儿我趴窗台,就见月光底,有个红子墙根晃,身形细细的,跟个纸似的。”
火堆渐渐了,火星越来越暗,槐树的子却越来越浓。
敬山往火堆添了把柴,火光重新亮起来,映得两脸都泛着。
他着守义眼底的惧,知道这事绝是空穴来风——守义打村长,胆子比般都,是撞见邪乎事,绝吓这样。
“明儿早,我跟你去沟子。”
敬山沉声道,“再去张头的坟前瞧瞧,说定能出点啥。”
守义点了点头,没说话,只是个劲地往嘴灌米酒。
风卷着坟地的土腥味过来,混着米酒的醇,竟有种说出的诡异。
槐树的枝桠,知何落了只鸟,突然“哇”地了声,扑棱着翅膀飞走了,惊得两都是哆嗦。
点多,两收拾了西往回走。
月光透过槐树叶的缝隙,地洒细碎的光斑,像撒了地的纸。
走到岔路,守义突然停住脚,指着边的方向,声音发僵:“敬山,你……”敬山顺着他指的方向去,只见沟子的方向,隐隐约约有个红子,立坟地的边缘,身形细细的,风吹,像是要倒似的——正是守义说的那个纸。
两站原地,僵了足足半钟。
那红子就立那儿,动动,像是盯着他们。
敬山捏紧了的筒,想照过去,却觉得胳膊沉得抬起来。
“走……走!”
守义拉了敬山把,两转身就往村跑,身后像是有脚步声追过来,“嗒、嗒、嗒”,轻得像纸蹭着地,却又清晰得让头皮发麻。
跑回村,撞守义家的院门,两反身把门关紧,顶门栓,这才瘫坐地,喘着气。
院墙,“沙沙”的声响还,像是有蹭墙,又像是有低声呢喃。
守义靠着门板,脸惨:“它……它跟过来了。”
敬山缓了儿,才勉镇定来:“别怕,院门栓紧了,它进来。
明儿咱们找村的支书,他懂些规矩,说定能有办法。”
那,两没敢睡,坐堂屋,点着油灯,守着把柴刀。
院墙的声响,首到亮才渐渐消失。
方泛起鱼肚,敬山起身走到门,透过门缝往,晨光熹,院墙空荡荡的,只有几片落叶地打转,像是啥都没发生过。
二早,两找了支书。
支书听他们说完,皱着眉想了半,才道:“张头生前扎纸,太入,魂儿说定附纸了。
他寂寞,想找个伴,就出来晃悠了。”
“那咋整?”
守义急着问。
“简。”
支书沉声道,“去张头的坟前,烧点纸,再烧两个纸,跟他说说话,让他安待地,别出来吓着。”
当,带着纸和纸,去了沟子。
张头的坟坟地的头,坟包长满了杂草,墓碑的字都模糊了。
支书点燃纸,又把两个纸火堆旁,嘴念念有词:“张头,后辈给你伴儿来了,你安待着,别再出来晃悠,吓着村……”纸烧起来,烟滚滚,飘向坟地的空。
两个纸火很化了灰烬,风吹,飘得漫都是。
火堆旁,张头的坟包,根杂草突然晃了晃,像是有点了点头。
从那以后,守义再也没见过那个红衣裳纸,院墙也再没有“沙沙”的声响。
沟子的坟地,又恢复了往的寂静,只有风吹过草叶的声音,和偶尔来的鸟啼鸣。
只是后来,每次守义和敬山槐树话,聊起那的纸,守义总说:“那纸的眼睛,像活的似的,这辈子都忘了。”
敬山则笑着递给他碗米酒:“都过去了,张头有了伴儿,就再出来了。”
风穿过槐树的枝桠,带着点米酒的醇,和坟地淡淡的土腥味,漫过那些沉默的坟包。
渐渐深了,槐压坟头,像是守护着那些藏乡的秘密,和那些没说完的鬼事。